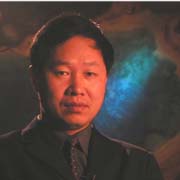一、宗教反邪教的理论基础
1、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是宗教反邪教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不同方面的既相互排斥、相互分离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以此分析无神论和有神论、宗教与邪教的关系,可以理解宗教反邪教何以可能。
首先,在同一性上,宗教和邪教是朋友。作为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宗教和邪教同属唯心主义,以此为前提的教义、教仪和教主,有很大同一性。这使他们在对待无神论世界观的时候,有在共同利益和宗教情感上的认同。从这个点上看宗教和邪教,他们是盟友。
其次,在斗争性上,宗教和邪教是对立的。在有神论内部,宗教、世俗迷信和邪教三者是互相斗争的。这种斗争性构成宗教反邪教的基础。
第三,在社会学意义上,无神论与宗教可以建成反邪教联盟。无神论反对有神论是有分寸区别对待的,在反对宗教、世俗迷信和邪教上并非平均用力等同视之。无神论对待宗教的敌意,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待世俗迷信的态度,主要是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上有限容忍;对待邪教,主要在社会学意义上法制的范畴里斗争。在社会意义、当然也包括文化和道德意义上,无神论和宗教有神论、世俗迷信有很大程度的包容。而在对待邪教上,主要针对其邪恶和破坏性,无神论的态度是强烈的敌意和毫不留情地打击。在这个基础上,无神论和宗教有神论和世俗迷信具有对邪教的共同敌意,无神论与邪教之外的有神论在对待邪教问题上,获得了有条件的有限的统一,无神论与宗教的反邪教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矛盾的同一性和特殊性、矛盾双方的既团结又斗争,成为无神论与宗教反邪统一战线的方法论基础。
2、用矛盾观点认识无神论与宗教的关系
矛盾的一方与对立面的斗争,是为了保持自身性状、求得生存发展的需要,宗教也是如此。宗教的自强,有赖于自我纯洁和对外力异化的抵制。
宗教是在宗教以外的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五大宗教坐大,是一宗教同他宗教、宗教与邪教、宗教与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
纯洁是自然万物的公理,物种的进化总是在自身纯洁与它种侵略的斗争中发展的,纯洁是物种存在和安全的需要。植物界如此,动物界如此,人类社会更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在生物学意义上杂交是必要的,但杂交必以不妨碍种群利益为基础,杂交是为了优化本种群而不是异化种群。在社会学意义上,文化的交流往往需要本土化就是这个道理。拿这个原理分析宗教,我们就能理解宗教的敌对和共存。
我们可以把儒、道、释共处看做是主流意识与宗教的和谐统一,由此获得历史上主流意识与宗教的和谐统一的范例。在这里,儒教显然不是以宗教的面目而是以非宗教的面目出现。以这个范例观照今天,就是主流意识与宗教的和谐的一面,我们的宗教政策正是如此。
儒家思想与佛教和道教的共存共处也是斗争的结果。政治力量的共存也是如此。多党共存是斗争的结果,因为政党也是排他的。有人认为羊群的持续发展需要狼群的存在,这是第三者的自然生态立场。站在羊的立场,没有希望狼来发展自己的道理。儒家思想与宗教的关系,与今天的无神论主流意识与宗教的关系,是十分恰切的类比。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理解是唯物辩证的。他理解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P341但同时他认为宗教存在是必然的:“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P1这里不仅指出了宗教的思想本质,而且说明了宗教的社会基础。在批判的基础上,无神论认可了宗教。
3、中国的宗教和邪教
狭义地说,一宗教都有视他宗教为邪教的意图和可能,在宗教与各种信仰和组织的斗争中,一些组织胜利了,一些组织消灭了。宗教的坐大,是斗争的结果——即宗教同无神论的斗争、宗教同世俗迷信的斗争、宗教同邪教的斗争的结果。在这个斗争中依然存在着对立统一。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更多的宗教和更多新兴宗教的原因。中国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或者说不是一个重视宗教需要宗教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宗法国家,宗族力量的强盛使宗教的势衰力微。中国又是一个儒学国家。这个有似于宗教又与佛道宗教有根本不同表现形式的学说,显然不是以超现实力量的信仰而是以道德的规制为主要内涵的,他张扬理性,藐视神学,不语怪力乱神,体现出德治的方法和理性的精神。牢固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学精神使宗教的生存受到抑制、限制和打击。所以中国纵使有过民间宗教活跃的时期,但进入社会稳定期后,由于政府的打击和社会意识形态各力量的钳制,民间宗教往往昙花一现。中国社会革命在短暂的民主革命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没有出现稳固持久的以自由民主为基本特征同时也伴随着信仰凌乱的可能的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很快在一个强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下获得统一。这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对今天中国新兴宗教不甚发达的理解。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同样的道理,我们就能找到1979年开始在中国出现了新兴宗教的兴起,以至发展出现像法轮功、中功等邪教的原因。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消极应对。一方面是我们必须对外开放,这样西方的思想随之而来以至泥沙俱下;一方面国内的变化也会造成人心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成就背后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政治改革的滞后、民生问题的凸现成为甚至邪教的关怀也能获得群众的社会原因。肇始于1979年的新兴宗教运动,一部分是外来的,一部分是本土的神秘主义作祟。前者如千僖年世界末日信仰,神秘的史前文明观点,相应的组织有如科学教、统一教、奥姆真理教。后者如各种神怪气功,如严新气功、中功、元极功、香功、华藏功、法轮功等等。
4、宗教反邪教的根本原因
宗教与邪教的本质区别是宗教反邪教的根本原因。
敌视是同类对他类的排斥,因为不同,所以不和。在宗教、世俗迷信和邪教共存的唯心主义的阵营里,斗争性仍然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我们说宗教反邪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之间的对立。“邪恶教派不仅是世俗社会的敌人,也是宗教尤其是传统宗教的敌人”,[3]P9宗教与邪教的对立,是根本利益的对立。
宗教和邪教在本质上的区别,是对社会、对信众的态度不同,是善恶之别。
宗教和邪教在教理教义和教主等方面,不构成本质区别。本质的区别在于正统宗教跟政府有很好的合作,这些宗教修为的目的是为了道德的完善和人生的终极追求,他们虽然也看到了社会现实的不完美但是他们本质上不是反社会的。邪教则恰恰相反,他们的理论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反政府反社会以满足私欲。宗教的修为是对于宇宙思考后的理论指导的结果,是世界观下的具体方法。佛教超世,主旨因果,教人向善,抚慰苍生心灵,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道教出世,主旨自然,追求“小国寡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其淡然隐身的态度是基于个人修身养性的考量,它并不影响别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道教清净无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由无为而达到无不为。以貌似消极的办法实现理想社会,目的还是改变世界,是积极的。邪教的目的是私欲,或者为了中饱私囊,或者为了败坏他所仇视的社会。以法轮功为例,他们的教义由他们自己概括成了“真善忍”,其中的真,一以对待社会之“假”,一以麻痹信徒,轻取他们的真心以便教主摆布;他们的善,是空乏的善,是幌子和遮羞布,因为以他们的方法,既无法达到内心的宁静,也无法达到身体的健康。法轮功的忍,并非宗教修为中的忍辱负重,而是告诉信徒在对抗社会的时候注意自保,以求来日更好地对抗社会。再如门徒会、全范围教会、观音法门、东方闪电、世纪神,鲜有追求道德完善苦行修为者,他们的手段,除了对抗社会,还是对抗社会,他们的目的,除了私欲,还是私欲。所以说,邪教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择其要者,就是亲和社会与对抗社会、众利与私欲的区别,概而言之就是善恶之别。唯其行恶,才是我们打击的理由!
5、无神论可以同宗教建成反邪教统一战线
宗教与无神论的根本不同,造成了他们的斗争。
在真理语境里,无神论与宗教水火不容,没有联合的基础。这是本体论的问题,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无神论就是唯物论,他们的观点符合世界的物质性观点,已被科学证明或即将证明,具有真理性。在形而上学语境里,无神论也将宗教与邪教等而视之。没有同一的理论前提。
但是在伦理学语境里,无神论与宗教获得了共性和互补。善的道德内涵是无神论与宗教同一的道德基础,虽然无神论讲究真实以至善,而有神论是在虚假的前提错误的方法下求善。无神论和宗教用不同的方法救赎心灵以满足不同人的心理需求。这就是无神论与宗教的同一性所在。同一构成共同利益,并排斥第三者,反邪教统一战线由此形成。
我们反对邪教的最大理由,就是他的伦理趋向,他的反社会反人类构成我们对他的打击。而邪教的反科学反真理,只当接受科学的批判而难于接受法律的处置。因为在现代法语境里,信仰自由是基本的人权。因此我们说,无神论反对邪教的理由,出现在伦理的范畴,而无神论与邪教之外的有神论的反邪统一战线,也基于此。通俗地说,宗教和世俗迷信是好一些的唯心主义,而邪教是坏唯心主义。宗教和世俗迷信有在法律规制下活动与生存的空间,邪教没有存在的法律基础。
哲学是关于本体、认识与伦理的学问。我们在伦理范畴里找到了反邪教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也就是找到了最高层次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它基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道德伦理观念上获得理论支持。所以我们说,反邪教统一战线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下进行伦理学具体分析的结果,无神论与宗教的反邪教统一战线,在理论上是正确的。
二、宗教的反邪教的原则与成果
1、宗教反邪教的原则
宗教反邪教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反对邪教,必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也就是理论的批判和实际的斗争,其操作各有政策的支撑和规制。
在武器的批判上,在实际的行动上,宗教的作为受到了来自法律的社会规范的最终也是无神论的制约。那就是,宗教不满足于他们的批判总是口头的君子行为,但是如果他们像邪教一样去宗教场所以外宣扬自己的宗教,去面向邪教信徒揭露邪教让邪教徒改邪归正,与邪教争夺信徒,则受到法律的限制。这就显示出宗教反邪教的现实局限性。宗教反邪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限的。
可不可以为了抑制邪教而适度放宽宗教的活动范围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放宽将受到无神论的强烈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无神论与有神论就不是联合而是斗争了。现行宗教政策既是无神论容让宗教活动地盘生存空间的结果,也是无神论限制有神论的活动地盘和生存空间的结果。意识形态的斗争终究是社会存在的体现,无神论没有理由也没有理论依据无条件退让,他们的容忍和妥协是有限的。认为制定无神论退让而使宗教的空间扩充的政策的努力,将受到社会存在的强力反抗。这就是说,一个科学飞速发展唯物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存在,有神论的地盘只会日益狭小而不会日益扩大。就政策上言,宗教文化整体被排除在先进文化之外,没有发展的政策支持。
由此看来,理论上的反邪,是宗教界反邪的主要形式。
理论反邪,揭露、声讨和批判,是宗教反邪的有利武器。邪教的本质导致了他的凌乱和粗糙,授人以柄,给宗教反邪提供了靶子。一个宗教的教义,必经时间的考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邪教之所以不是正统宗教,就在于他缺少历史、没有经典,他们的教义只能是偷窃和拼凑。其中偷窃篡改自正统宗教者,被偷者最能识别,借用拼凑自世俗迷信者,宗教界也能识别,揭露和批判就有了条件。新时期反邪教运动以来,宗教界反邪教的主要活动就集中在从理论上识别、揭露和批判上。
理论反邪教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
第一,宗教可以抵制邪教对宗教合法利益的侵略,在邪教争夺宗教信徒的时候,宗教可以义正词严地还击。
第二,宗教可以还击邪教对于宗教理论的诋毁和污蔑,包括邪教对宗教教义的借用和篡改,宗教可以正声明无情揭露彻底批判。
第三,宗教可以更加纯洁自身树立良好形象在政策允许的范围里争取信众。虽然宗教的活动空间是有限的,但文化信息的传播是多途径全空间的。宗教可以树立更好的道德形象,如基督教一样在爱国旗帜下的“三自”,宗教也可以在爱国爱民溶入社会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即使是传播宗教场所的限制,也不是绝对的与有信仰倾向的群众的隔离,因为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充裕,人们的前往宗教场所旁观或者参加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加,而无心宗教的群众通过旅游或媒体信息获得宗教文化进而选择宗教道德以求心灵寄托的机会也越来越大。这样,宗教的楷模作用就很重要。
而在以下方面,宗教反邪教是不可作为的:
第一,宗教不可能与邪教进行信仰资源的实地竞争,他们不能深入邪教活动区域也就是世俗群众之中去争夺信徒,更不能在邪教没有进入的地方抢占信仰市场。
第二,宗教也不能在批判邪教的同时在宗教场所外宣教。因为宗教场所外宣教为国家法律所不允。实际的例子是,在国际反邪教斗争中,宗教界和社会各界曾经多次到邪教活动区进行针锋相对的活动,但这样的活动是以关爱协会的名义,以不宣教为底线的。
第三,宗教也没有能力针对邪教进行组织打击。打击邪教只能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由司法机关进行。
2、宗教的反邪教成果
陈星桥在《略论宗教界在反邪教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4]P38-39列举了佛教反法轮功邪教的历程和成就,由此可见宗教反邪教之一斑。
法轮功肇始于1992年,从1994年开始,佛教界就关注并批判了法轮功。作为哈尔滨市佛协副秘书长,陈星桥居士在1994年听了李洪志宣讲“法轮大法”后即向有关部门举报李洪志假佛行骗。浙江台州佛协主办的《台州佛教》月刊1996年刊出了数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可以看作是最早关注和批判法轮功的成果。该刊从第5期到12期,发表了智觉《〈转法轮〉——毁人慧命的邪魔典籍》、刘继汉《〈转法轮〉是何等书?——兼评李洪志其人》、张秉全《〈转法轮〉是一册毁谤佛法的坏书》、卢守中《转正法轮》、金刚剑的《“法轮功”是披着佛家外衣的邪教魔功》、常州天宁寺佛学院《“法轮”怎么转到雷锋的头上》、长春市悟心等《“法轮功”不是佛家功》;王文辉《评李洪志的两面派手法》。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协会的妙华法师、上海市佛教协会的郑颂英老居士等佛教界人士也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法轮功问题,表达佛教界对法轮功歪曲、利用佛教的义愤。
1997年以后,《上海佛教》、《广东佛教》等地方佛教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上海佛教界还收集有关正面介绍佛教“气功”和揭露、批判法轮功的文章汇编成《摧邪显正集》在教内流通。1998年元月,中国佛教协会专门召开了一次针对法轮功问题的座谈会,1998年6月,陈星桥《佛教“气功”与“法轮功”》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成为法轮功被取缔前惟一公开出版的揭批法轮功的书籍。
宗教界也是最早响应中共中央取缔法轮功决定的界别之一。1999年8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医院就法轮功问题发表重要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取缔法轮功的决定。10月28日,首都宗教界和社科界部分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部分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到场,严厉批判法轮功邪教。
2000年11月13日,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发起人包括庄逢甘、龚育之、潘家铮、傅铁山、王家福、圣辉、何祚庥、郭正谊、王渝生等,他们来自中科技界、社会科学界、医学界、法律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其中来自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傅铁山主教和来自中国佛教协会的圣辉副会长成为副理事长。此后,宗教界联合或单独进行了一系列揭批法轮功的活动。2000年8月26日,五大宗教领袖联合访问美国,宗教界揭批法轮功活动走向世界。
三、无神论在宗教反邪教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
1、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我们的宗教政策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要体现为对宗教的形上认识、对宗教的社会学认识、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我或是再度丧失了自我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2]P1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中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5]P348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6]P666-667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宗教的道德意义,即宗教的社会意义。
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P1心灵的抚慰和终极关怀,被马克思形象贴切地用“鸦片”形容出来了。
第三,信仰自由是信仰者个人的自由,国家允许这样的自由但不参与宗教。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因此不同人的意识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特点。人脑是个体的人脑,支配自己的大脑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在这个基础的信仰总是自由的。所以马克思说:“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7]P34
列宁也指出:“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8]
第四,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宗教。
马克思在阐述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宗教的态度。他说:“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图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脱出来。” [7]P34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写进了“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后来,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倾向的抬头,有人把论点曲解成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当时恩格斯虽然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直接争辩,但却采取了正确叙述的方式反对了这种观点。恩格斯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实行宗教对于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9]P247-248)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中指出信仰宗教自由的同时,强调了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他说:“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 [8]这里明确表示,社会主义者必须是无神论者,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对于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8]
列宁也指出:“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8]
第四,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宗教。
马克思在阐述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宗教的态度。他说:“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图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脱出来。” [7]P34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写进了“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后来,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倾向的抬头,有人把论点曲解成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当时恩格斯虽然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进行直接争辩,但却采取了正确叙述的方式反对了这种观点。恩格斯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实行宗教对于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9]P247-248)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中指出信仰宗教自由的同时,强调了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他说:“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 [8]这里明确表示,社会主义者必须是无神论者,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对于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8]
2、无神论在反邪教统一战线中的主导作用
邪教不是宗教,这是从正与邪的角度来识别的,就如同坏人不是好人。但是,正如邪教和宗教有本质的区别一样,邪教和宗教又是有本质的联系的,这些联系表现在:第一,都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都信仰超自然的力量。第二,都有教主崇拜的形式。第三,都在道德上强调终极关怀。第四,具有同样的社会基础。“只要有宗教的市场,就可能有假冒伪劣的邪教存在。如同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样,邪教也具有这五性。”[4]P39
无神论是有神论的天然敌人,无神论所针对的,是一切有神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并非针对某一特定的宗教、世俗迷信或邪教。我们谈朋友,是在信仰的社会意义范畴里,无神论与宗教的同一性和无神论与宗教同邪教的斗争性,是在信仰的社会作用这个范围里的矛盾理解。合作也好,斗争也好,都在这个范围进行。离开这个条件讲无神论与宗教的合作,都是无视矛盾特殊性的表现。
世界观的优劣评价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站在科学的立场,只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才是科学的世界观,因此,无神论应该而且能够在反邪教同意战线中起主导作用。无神论反邪教包括了独立行动的部分和联合行动的部分,独立反邪教是最基本的形式,这是由无神论的世界观本质决定的,但无神论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高度之后,他们懂得把握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影响,进而把联合反邪作为反邪教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补充。
3、宗教的反邪教行为受到自律和他律
宗教在反邪教中的地位重要,作用不小。这不仅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也获得了实践的验证。但宗教反邪教同样存在受到各种阻力、无法随心所欲的问题。宗教反邪教必受到自律和他律。
在宗教界,陈星桥对“某些人在理直气壮地用无神论和所谓科学批判邪教时,其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宗教” [4]P38表达了不满。上海道教协会史孝进先生提出增进宗教反邪的观点。他认为邪教痴迷者中有相当部分有宗教信仰的倾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他们有了解宗教知识的渴望,但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传统正信宗教,缺乏识别、判断何为正教,何为邪教的能力。因此,“宗教界人士可以参与对这些对象做一些说服宣传,以传统宗教的教理教义思想、博大精深的优良传统文化感化他们”“使他们重新树立信念。”由此,“我们在举办各类转化学习班时可以考虑邀请一些宗教界权威人士参与,让宗教界人士参与到转化工作中。”[10]史孝进的观点虽然谨慎,但显然也存在扩展宗教活动范围的企图。
宗教反邪教是否应该有更宽松的环境,或者宗教是不是可以在更大范围发挥他的作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宗教的作用与我们的态度问题。干朝端在《从犯罪学的视角看有神论》中指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宗教及其对宗教的信仰可以抑制犯罪的发生”,因此“从政治角度来衡量,对无神论宣传”要“谦抑”。[11]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在社会各界,尤其是部分反邪教工作者之间,还有一种更直截了当的观点,就是利用宗教反邪教,提出与其信邪教、不如信宗教的观点。
宗教界希望为反邪教事业做更多工作的追求,是可以理解的。学界认可宗教的社会意义,也是正确的。与其信邪教、不如信正的观点,更没有逻辑的错误。这些集中在扩大宗教反邪范围和力度的观点,虽然立足点不同,出发点有别,但都是有他的片面性,一个方面的正确无法掩盖另一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宗教的地位与他的社会存在相一致。
宗教的地位与宗教的社会存在状况相一致,不存在由谁给予和让授更多权力的情况。只有基于社会存在分析社会意识,才能理解社会意识形态。宗教的权力和义务,虽然是经由意识形态规范、并进入了法律法规的体系,但之所以是这样,是无神论和有神论斗争的结果,是与宗教的实际情况相一致的。宗教的地盘和活动空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只能这样。如果宗教足够强大,宗教社会存在将会导致它的对手阵地的失守而获得地盘的扩充,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力量,人为扩充后,仍然不免再度失守。
其次,宗教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宗教政策。
充分发挥宗教在反邪教中的作用,必须注意尺度的把握。这个尺度就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不可逾越。国家政策不允许在宗教场所以外宣教,因此也不能为了反对邪教而在非宗教场所与邪教争夺信众。
第三,用宗教挽救邪教信徒不符合道义要求。
与其信邪,不如信正的观点,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观点,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有其存在的土壤和现实基础。但是,在劝信问题上,这样的观点还是有问题。既然劝人向善,则同样存在两利相较取其重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需要精神寄托和心灵抚慰,则我们的立场是帮助他们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宗教的信仰和一种唯物主义的信念,利弊不辩自明。俗语说,要给就给最好的,断没有明知有缺陷却推销、明知有最好的却不给的道理。我们的宗教政策正是基于“最好原理”设立的,他是我们宗教工作的指南。
无神论对宗教是有条件欢迎和允许、无条件抵制和批判的。无神论欢迎宗教反对邪教的立场。但无神论断没有为了反邪教放任宗教借力反邪或者以假制邪的道理。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利用宗教反对邪教的方法,是背弃道义的无耻的行为,他和公安放任一个较好的黑道帮派与一个更坏的黑道帮派火并而渔利没有两样。在这里,火并是一回事,放任是另一回事。公安没有放任的理由。
第四,过多依赖宗教反邪教的观点不符合实际。
无神论不仅应该同宗教结成反邪教统一战线。同时,无神论也应该全面研究宗教、邪教、世俗迷信之间的关联,研究他们之间的联系,研究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研究邪教何以热衷于借用、窃用宗教和世俗迷信,这是与无神论与宗教反邪教统一战线方向相反的一个大课题,但同时也是重大课题。
无神论对宗教反邪的过多依赖,是与他真理在握信心满怀的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无神论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有神论,更罔论有神论中的邪恶者。
由此观之,宗教反邪教既是可能的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反映的正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有限性本质。解决问题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能是无神论的出击。崇尚科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消灭邪教的思想路线。在法制的范围里,打击一种深入群众的邪教传播方式,扫除邪教的活动空间,摧毁邪教的组织,是反邪教是行动路线。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王清淮等.中国邪教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
[4]陈星桥.略论宗教界在反邪教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J].中国反邪教通讯,2010.12 .
[5]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8]段启明.关于青少年科学无神论教育的几个问题[EB]中国反邪教网.学术交流.
[9]P247-248(列宁:《论工人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
[10]史孝进.发挥传统宗教的积极作用,抵制和防范邪教势力的传播和发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打击和防范邪教——中国反邪教协会第五次报告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
[11]长江日报.2004.4 .22.
(湖南省第二届反邪教理论研讨会论文,发表在《反邪教论坛》时杨慧元署名第一)
[11]长江日报.2004.4 .22.
(湖南省第二届反邪教理论研讨会论文,发表在《反邪教论坛》时杨慧元署名第一)